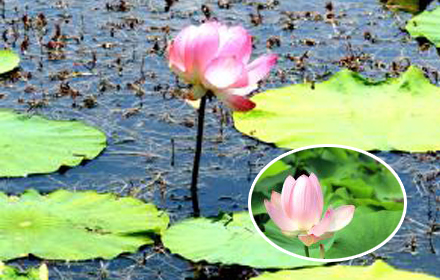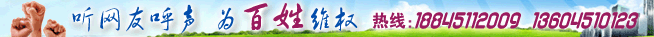东北网手机版 3g.dbw.cn
科学研究是教师(医生)成为大师(专家)的必由之路。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些绝对,但只有当深刻理解了大学的本质和使命时,才能真正领会其真谛。我院的办学定位为“面向基层,培养应用型医药卫生人才”,一脉相承下来就自然属于教学型。但我认为,教学型院校不等于不搞科研,一个科研上不去的本科院校一定不是一所优秀的大学。只有与同类不同,只有超越同类,才是特色,才能与众不同。齐医,一定要让科研崛起,与众不同。
教学型院校到底搞不搞科研,或者说是教学和科研两条腿走路,还是一高一低跛行,不同大学的管理者有不同的看法。从早期认识的差别到后期开展科研工作面临的种种困难,可以说,我院的科研道路是不平坦的。我始终坚持,只要是本科院校,不论是什么“型”,都应教学、科研两条腿走路。
在“985”、“211”大学总是强调教授上讲台,而在我们学院如何让教师重视和开展科学研究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或出于对科研先天的青睐,或出于对大学内涵的理解与责任,在推进科研工作方面我一直激情满怀,不移不辍。在老校区时,学院只有一个简易的中心实验室,但好像没有任何专门的研究所或研究室等科研机构。在我分管科研工作期间,请求市科技局批准我院成立齐齐哈尔医药研究所。用“请求”两个字,是因为市科技局并不具备批准非市属单位科研机构的职权,实际上,那只是一个非正规的“批准”。若拿到今天,说不定还要给他个“过度作为”的问责。第一任所长是我自己任命自己,还有一个教师被我任命为兼职副所长,没有专职人员,没有科研经费,但那是我院发展史上第一个“科研机构”。记得在填报申请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材料时,国家级课题为零,被SCI等三大检索收录论文为零,获省级奖励为零,举办省级学术会议为零,译著为零,科研经费以万元为单位不超过两位数,从这张表格足以看出我院当时的科研状况,结果不言而喻。面对如此薄弱的科研基础,没有气馁,没有泄劲,科学研究不是百米冲刺,而是马拉松。我们像愚公移山一样,一步步向前推进,不但要铲除客观条件上的太行、王屋二山,还要推倒认识观念上的喜马拉雅山。
在建设新校区时,尽管资金十分紧张,但还是下定决心建一个研究基地,于是,才有了一座科技大楼。时至今日,这座7000多平方米的医药科学研究院大楼已经容纳不下现有的研究室,又将刚刚启用的4000多平方米的实验动物中心拿出一半用作科研用房。建立了天然药物抗肿瘤研究所、多基因病研究所、微生态工程中心、卫生检验中心及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等33个科研机构,设立专职科研编制,配备相应仪器设备,提供专门科研场所、专项科研经费等等。通过柔性人才政策,聘请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邱长春教授为多基因病研究所所长、首席专家,提供一层楼作为研究场所,建立了相应的科研团队。该团队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和省级项目,并在世界著名杂志《Science》专刊上发表了以我院为第一署名单位的学术论文。为了加快科学研究步伐,学院制定出台了《齐齐哈尔医学院“2011-2015”科学研究发展振兴纲要及2020年远景目标》以及一系列鼓励支持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的政策措施。启动院内科研立项,对获得的课题给予经费配套,实施项目奖励、论文奖励、成果奖励及专利奖励,有课题者可脱产进行课题研究,实施科研助理聘任制度等等。其中有一项是不足以称为措施的措施,看上也去很离谱,即为了更好地开展科研工作,下令将研究所所有实验室的门锁取下。一把锁究竟与科研有何关系?无论怎样想,门锁和科研都扯不到一起去。但恰恰是一把锁改变了科研的命运。近年来,对陆续引进的一些大型仪器设备实施专人管理,但使用率一直不高,许多教师不了解这些仪器设备能检测哪些指标,甚至一些教师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仪器设备。经过仔细观察,这项再常规不过的管理措施就是影响仪器设备使用的最大障碍。换上玻璃门,取下门锁,只要在走廊走过,就能看见所有的仪器设备,任何科研人员,无需申请,可随时自由使用。随着这些先进仪器设备使用率的不断提高,科研质量和科研水平也随之明显提升。能够观察出这样一个细节,足以见得为了把科研搞上去,真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了。细节决定成败也就在这里。
为山者基于一篑之土,以成千丈之峭;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经过几年锲而不舍地努力,学院的科研工作发生了巨大变化。现有专职科研人员60多名,科研仪器设备总值6800余万元,在研经费1131万元。“十二五”期间,科研经费达2529万元;获得各级各类科研项目近800项,其中国家级项目20项;发表学术论文2724篇,其中被SCI等三大检索收录论文255篇;获得科研奖励262项,其中省部级奖励11项;获专利授权228项,还实现了部分成果转化。科学研究的巨大进步,已成为学院的一大亮点,为申请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开展研究生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改革开放持续升温的90年代,中国大地上热映着一部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使人们一时间将编辑部看成是社会上最具思维、令人向往的文化单位。在同一个时代,齐齐哈尔医学院也在上演着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其形成的小企业文化是我在当时大会上给予表扬的唯一部门。整个编辑团队6、7个人,年轻而富有活力。开放的思维、积极向上的态度、改革创新的精神是这个团队小企业文化的核心。当时,学院的期刊社像其他高校的期刊社一样,属于教辅部门,人员工资和办刊经费由学院供给。期刊社办有《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和《黑龙江护理》两本杂志,一本是季刊,一本是双月刊,两本杂志合计一年出版10期。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期刊社提出了走向社会、开放办刊的思路。
1998年,期刊社尝试性地依托《黑龙江护理》杂志在大连举办了一个全国护理学术会议,仅有30多人参加,但也基本实现了以会养会的资金平衡。这次会议后,学院的一些人在不同场合有一些议论,甚至认为这是在利用办刊经费旅游。但我还是给予了及时的鼓励和肯定,因为像我们这样一个地处偏远地区、名不见经传的院校期刊社能够举办全国学术会议实属难能可贵,这可能是医学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全国学术会议,单凭这种敢闯敢试的精神就应给予肯定。为了转变大家的思想认识,在次年研究学院年度预算的会议上,还把期刊社的年度工作计划也上会讨论。正像有的领导所说:“学院的办公会还从没讨论过一个部门的工作计划。”事实上,这是我作为分管院长事先的建议和安排,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那以后,期刊社到外地举办会议就成为一项正常年度工作,也得到了普遍共识。我认为,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可以开阔视野、网罗专家、结识同仁、扩大期刊社及学院的社会影响,这是走向企业化办刊之路的探索,为后来期刊发展打下了决定性的基础。
由于学术会议、编委会议等活动的带动,期刊的稿源不断增多,《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黑龙江护理》都变成了月刊。随着刊期发行量的增加,期刊社的日子也红火起来,再创办一个新杂志的想法应运而生。具体办什么杂志?本着“办刊为促进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服务”的思想,经过思考,拟创办一个精神类杂志,定名为《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这是基于办刊既要依托学院的优势专业——精神医学专业,同时,期刊也可以促进精神医学专业的发展。当时,从省内到国家正处于整顿期刊时期,对新期刊审批基本告停。我与胡凤岚、沈黎两位社长多次奔赴省科技厅和国家科技部等有关机构,不断地向相关部门说明办刊的意义和对学院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依托精神医学专业办好期刊等等,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进科技部的大门。反反复复,几经周折,我们只好期待时间能够带来幸运。功夫不负有心人,正当我们在张家界举办一次全国编委会议,带领专家即将登临天子山顶峰之时,突然电话里传来了好消息,《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杂志通过审批了,筋疲力尽的大家听到这一消息后,顿时精神倍增,一鼓作气登上了顶峰。
进入2000年,人们为迎接新世纪而欢呼,美国向全世界宣布,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基因框架图谱绘制完成。一时间,关注健康、向往创新的激情不断释放出炽热的火焰。一个大胆的想法开始在期刊社酝酿——到北京办刊。齐医既不是“985”、“211”的名牌大学,也不具有综合性大学的经济实力,这个想法不仅对学院的决策是个挑战,也实在是超出了一般大学人的思维定式,这是一件大事。举办学术类期刊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文化事业,受地域的影响很大。为了提高办刊质量和水平,必须建立一个由优秀专家组成的编委会和形成一个高水平的作者群体,保证杂志有源源不断的优秀论文稿源,这在地域偏远的北方是难以实现的。走出去,到北京办刊是正确的选择,也是期刊发展的长远之路。学院领导对此没有异议,作为分管期刊工作的领导,我对此坚决支持,时任院长韩一眉最后拍板决定。一个多么天方夜谭的想法竟然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才有了齐医期刊社的今天。到北京办刊是决定了,但办刊经费、办刊场所、生活居住场所和工资奖金问题等等一系列难题都摆到面前。我主张,既然走出去,就要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企业化经营之路。在讨论如何去北京办刊时,我说:“现在大学的期刊社如同温室里的花朵,不愁吃不愁穿,但到北京去闯荡,如同置身亚马逊丛林,只有披荆斩棘闯出一条道路,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就看你们了。”两位期刊社的领导既渴望走出去,又感觉压力巨大。时至今日,可以说,期刊社已从危机四伏的“亚马逊丛林”闯出去了,并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
在北京办刊的起步阶段十分艰苦困难。在朝阳区5个人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民宅,白天是办公地点,夜里是居住场所。洗漱做饭虽然拥挤,还可对付,上卫生间排号等马桶却成了尴尬的事。因此,无论冬夏,男士们只好下楼到小区的公共厕所方便。但他们汇报的是工作生活条件都很好,从没说起什么困难。直到我有一次去到那里才知道他们是克服了多少困难,凭着一种进取精神在努力拼搏着。实际上,除了生活、工作条件上的困难之外,组建编委会、聘请知名专家、组织稿源等方面都步履维艰。两位社长带领小团队不屈不挠,乐观前行,期刊一步步在发展。此时,学院从长远考虑,决定为期刊社购置一处办公地点,韩院长派我和姜连清副书记去北京考察选址。先后看了期刊社当时租住的房屋,又看了雍和宫附近的现房及其它地点,期刊社有所倾向朝阳区租用的那套房屋,因为能够现得利。经短暂讨论,选定了SOGO后面的一个小区。当时,楼房还没建成,正在打地基阶段。将一梯二户的两套精装修房同时买下,共300多平方米,花了270多万元。据说按现在的房价来计算已增长了10倍,达到近3000万元。
十几年的光景,期刊社北京部由5名员工发展到70多人,实现了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企业化经营模式,已经成为大学期刊领域改革成功的典范,齐医也成为在北京办刊的全国唯一一所高校。现在,《黑龙江护理》早已更名为《中华现代护理杂志》,进入中华医学会杂志系列,《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进入中国医师协会杂志系列,《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也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三本杂志每年合计出刊78期。期刊社已远远超出了单纯办刊的职能,现已成为学院对外交流联络的平台,也成为社会了解我院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全球化背景下,学院期刊社正在启动创办英文版期刊计划,“编辑部的故事”还在延续……
申硕的路太过坎坷,没有任何一件事让我如此迈不开步。关于硕士学位授予权,一直是横在我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早期是由于学院自身条件不够,后来教育部的一项政策变动,让我院申硕道路又延长至少十年以上。曾有过两次申报的机会,但未能实现。一次是在专家组认为我院具有相对优势的情况下,因省内高校之间的历史问题而“落榜”。另一次是国家学位办启动专业学位评审,尽管全力以赴,但以全国5所民办院校成为我国首批研究生教育单位的热点新闻而终结了我院在申硕道路上的又一次冲锋。面对这种局面,内心充满着无限的无奈。领导的胸怀不在于容得下成功和荣誉,更在于容得下失败与无奈。不抱怨,不放弃,虽然我们没有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但我们要比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做得还要好。我指导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于2004年顺利毕业并取得硕士学位,第一名博士研究生于2009年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第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也于2009年顺利出站。自学院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佳木斯大学、新乡医学院、皖南医学院等国内院校联合培养研究生至今,共有52名教师被聘为兼职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共培养硕士研究生137人、博士研究生8人、博士后研究人员10人。“能不能被授予硕士单位,是国家政策的事,能不能搞好科研是我们自己的事”,这就是我的信念和在全院大会上的宣言,它一直在支撑着我们在申硕的道路上努力前行。我坚信,“十三五”期间,我们一定会搬掉心头上的这块石头,实现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院校的目标,跨过通向医科大学金字塔的最后一道门槛。
- 24小时新闻排行榜
- 曝光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