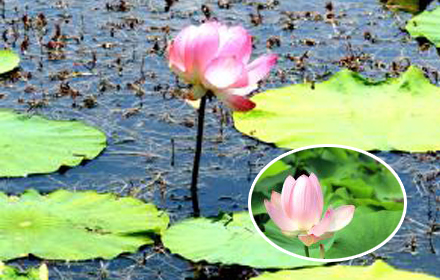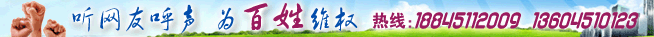东北网手机版 3g.dbw.cn
第五篇追求卓越
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告诉我们,人的需要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当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后,就会向高一层次迈进,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内动力。不仅人是这样,一个组织、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国家亦是如此。追求卓越不啻为校长办学征途上的不熄灯塔,亦是其为之倾情尽力的宿愿。然而,大学的卓越是什么?如何去追求大学的卓越?其实,这种思考从未停止,今后也必将永远延续,但答案永远属于校长内心世界永恒的追问与求索。
办好一所大学,不仅要解决好“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
还要深悟大学“是什么”和“为什么而存在”的问题,这就是办学理念。大学的领导们一直都在追求卓越,追逐区域的、国家的、世界的一流大学,彰显自身的、地方的、行业的办学特色,大师、大楼、学科、专业,以教学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一大堆关键词筑起了大学校长追求卓越之梦。
在我看来,卓越不是一种标准,而是一种境界。追求大学的卓越应体现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方面。追求形而上的卓越就是致力于使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培养模式以及价值观念和校风等大学文化的内涵始终处于卓越状态,追求形而下的卓越就是要保证让学科、专业、教材、论文以及各种办学条件等看得见的指标达到卓越的程度,忽视哪一个方面都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由于一些大学过度追逐后者而忽视前者,这就导致了哈瑞·刘易斯教授认为的《失去灵魂的卓越》。刘易斯在哈佛大学任教30多年,并作了8年哈佛学院的院长。在他看来,哈佛失去灵魂卓越的主要方面是忘记了教育的宗旨,而过多地关注了能够给大学带来显赫声誉的各项指标,包括像竞技体育那样所有美国大学都不可忽视的项目。而对于如何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培养成为二十几岁的青年以及让他们如何成为社会的合格公民却没有做到全心全意。无论刘易斯怎样说,在我心中哈佛大学都是世界顶级大学的典范,然而,他的观点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哈佛大学都失去了“灵魂的卓越”,时下,一些大学林林总总的现象是否也关乎失去灵魂的卓越?大学变得越来越像政府机构,热衷于官场文化,追求官阶胜于追求学术,“学而优则仕”成为那么多学者的价值取向;大学变得越来越像商业公司,功利主义泛起,诚信文化荒芜,学术不端、考试作弊在不小范围内流行;大学变得越来越像工厂,把学生当做流水线上的一个产品,偏于注重实用技术和生存本领,而缺乏人文情怀和职业情感的培育;大学变得越来越像竞技场,喜欢在万众面前进行百米冲刺的欢呼雀跃,而不愿坚持在那漫长崎岖的小路上进行默默地长跑;大学变得越来越像戏剧场,浮躁肤浅流行,表演表现热烈,甘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潜心于学术的精神成为稀缺,等等。我们的医学院是否也在其中?蔡元培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络众家之学府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有大楼、教室、实验室就是大学吗?但无之一定不是;有大师、教授、学者,就表明了大学存在的意义吗?但无之又何以为大学;有学科、专业、论文、著作就表明了大学之大吗?但无之又怎能说它是一个内涵充盈的大学!在校长心中,抑或注定要把大楼之类、大师之类、学科之类、论文之类统统地装进去,甚至也必须装进工人师傅、管理干部和利益相关者……但无论装进什么,装进多少,唯独不能忘记不装有让大学具有存在意义的学生和由此而发的大爱。尤其重要的是,更不能不深悟装进心中这千头万绪背后的本然!德国学者阿伦特说,“制造一张课桌的意思,不是增加一项财产,而是创造一个参与沟通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一名优秀校长应当竭力营造和维护的。”
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喜欢新事物胜于喜欢旧事物,但在校园内,一些沧桑的老树却让齐医人更能触景生情。在学院搬迁时,将饱历沧桑的山杏、山梨等一些老树移来,在学海边已蔚然成林,成为象征齐医脉络的思园。矗立在爱园纪念广场上的由老校区大门两侧浮雕砌成的纪念墙,在记述着齐医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的历程。校园里的大医路、大医广场,大医文化时光隧道等处处彰显着大医文化的内涵。以仁园为依托的人文哲学板块、以德园为依托的医德文化板块、以爱园为依托的大爱文化板块、以思园为依托的历史传承板块、以大医文化时光隧道为依托的医学精神板块以及以林园为依托的生态文化板块,形成了以仁、德、爱、思为灵魂的“大学至善,大医精诚,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的理念。时任省教育厅副厅长辛宝忠走在校园中说过,“齐医校园上空处处飘荡着大医文化。”文化之与大学犹如阳光之与禾苗,照耀其茁壮成长,犹如血液之与人体,滋养其健康发育。如今每一个生活在齐医的师生,都时时处处沐浴着“行不言之教”的大医文化。
- 相关新闻
- 24小时新闻排行榜
- 曝光台